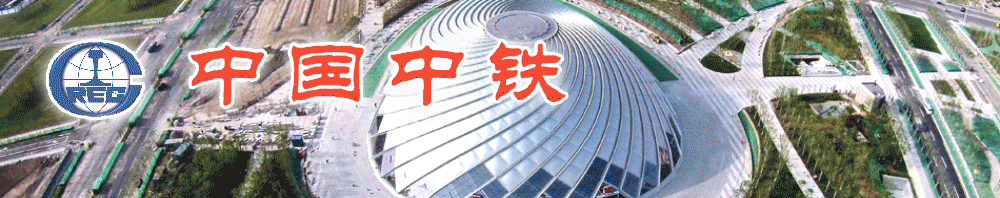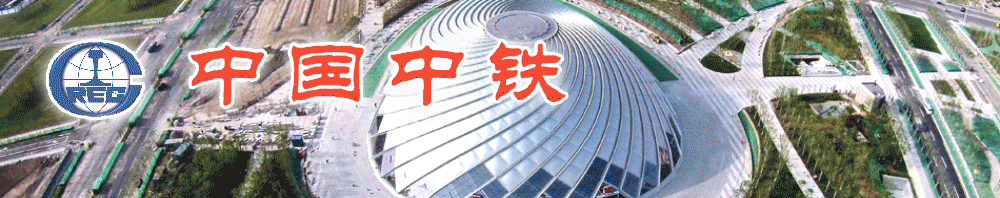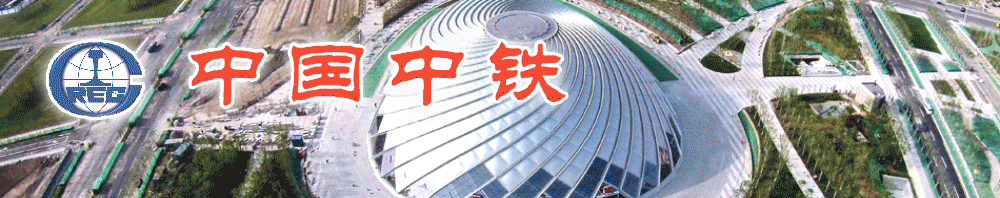东北的雪,好像下了很久很久。
吴青青睡了两天东北大炕,整个人的尺寸都似扩大了两圈,跟发面似的。房东大婶对待他们这些为人民修建铁路的工人非常热忱,每次烧炕,都添足了柴火,好像恨不能借三昧真火来用用。
主管们照例每天起大早去作业队长屋里开会。姓常的安全主管一开门,迎面卷来一阵风雪,人一激灵,望望灰青色的天光里迷迷蒙蒙的飞雪,不由发了几秒的愣怔,埋怨道:这龟儿子天气,咋个干活哟!随后将笔和本子往怀里一藏,出了门与众人一起,相跟着进了作业队长的屋子。十来个爷们,八成人都抽烟,大伙儿在云雾缭绕里手不停闲地在笔记本上唰唰记着,重点还是物资问题,气候恶劣,运输困难。负责物资的老毛压力很大,愁得顾不上洗刷,整天胡子拉碴的。
雪下到中午就停了,阳光出来,照得大地一片银白色的晶亮。吴青青戴上帽子、围巾、手套,端个相机就出门了。刚刷出来的洞门在山坡背风处,没被大雪完全覆没,留着粗粗的一个轮廓,好像在东北的日子有了奔头和向往。
工区宿舍终于建成了,吴青青终于盼到了标准化卫生间,老乡的茅房对于用惯了抽水马桶的她来说,简直就像一场不分昼夜的噩梦。
某天早晨,她去上厕所,一转弯,没见着亲切的标准化卫生间,只有一地七零八落倒着的彩钢板,有人在喊:同志们不好了,厕所被刮跑了!
吴青青在东北大地无止无境的天寒地冻里,时常会生出一种渺茫,好像正常的生活将她遗弃了。
倏忽间,衣裳渐渐穿得少了,中午还能穿个裙子臭美臭美,即使周围全是成堆成堆的砂石料混凝土,没有咖啡、钢琴、歌剧演唱会,也要灿烂灿烂,才不枉青春年华的繁花似锦。
东北的秋,短得更像一个梦,美丽的梦,七彩斑斓,五光十色,丰厚而柔美。
来了几场风,下了几场雨,林子一下子又消瘦了,过了寒意深深的中秋,雪就来了。
雪是晚上十点多下的。当天中午,工区里开了个会,正式宣布冬休。散会之后,吴青青就躲在屋子里一直没出门,想着漫长的冬休心里有些恍惚。冬休的第二天,车子拉满回家的行李,走过搅拌站,走过加工厂和洞门口,一片寂静。原先这里还充满各种机械的嘈杂,电焊的火花,工人忙碌的身影……
车子行驶在白雪茫茫的大地上,吴青青突然很想去看看东北大地上的第一条铁路——中东铁路,想去看看那一根根安静铺陈着的枕木,是不是也覆满了静静的雪?那窄小的轨道,在没有列车行驶的时候,会不会告诉人们,很久远很久远的那些故事?那些永远不该被遗忘的故事,即使被一场又一场厚厚的白雪覆盖,也掩盖不了它们沉淀在每一根枕木体内的声音。这些声音,是吴青青他们走下去的力量。